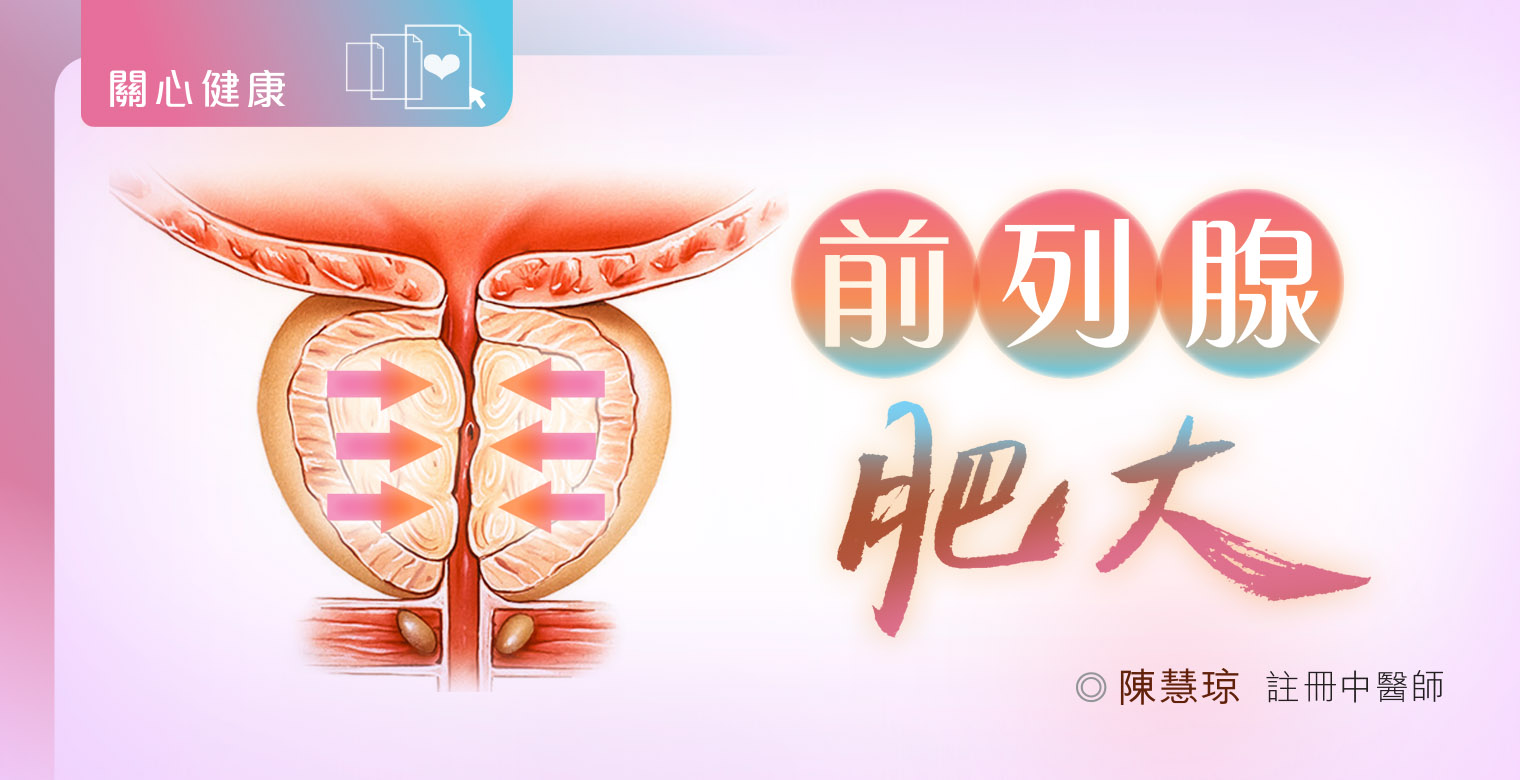70年代的香港,經濟發展進一新階段,很多香港市民都視為機遇之時,但對於我們這個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庭,卻要絕處求生:是錯誤的選擇抑或自闖困境?還是生不逢時或是命中註定?無論如何,反正,造就了今天的我。
初到貴境,身心受困
出生於中國廣西,自小說普通話的我,六歲那年就和妹妹離開愉快的童年地,隨著父母來港定居。爸爸在國內從事演藝事業,既是有名氣的演員,又是導演,來港後沒有機遇,找不到本行,只能出賣勞力,做地盤工人,好養活一家;大學外語畢業的媽媽在畢業後便生了我,來港後,她的學歷不被認可,只能以手藝賺取生活費,做製衣工人。我作為大家姐,來港不到一年,就因為爸、媽要工作,年紀小小就成為家中的照顧者,煮飯、洗衫、邊照顧妹妹邊讀書、做補習老師賺點外快等不在話下,就連之後出生的妹妹,也是我帶她往健康院,更因此被人誤會,嘲笑我是未婚媽媽。
外來嘲笑聲不絕,就連廣東話說得不純正,也是嘲笑的原因,所以,內裡的挫折感也不絕。我不敢告訴人我住在木屋區;縱然曾經入住親友家,也覺得是寄人籬下;颱風日子,要四出尋回被吹走的屋頂;火燭,要趁時搬走貴重物品逃離火場,也曾不自量力的想搬走家中最貴重的雪櫃……那些日子,生活極不安穩,很不開心。
可惜,本可以作支撐、陪伴我和安慰源頭的爸、媽,不但未能扮演這角色,沒給我一個愛的家,更令我變得充滿恨意。爸、媽勞苦工作,疲於奔命去賺錢養活,為了維持一個家,我們聚少離多,我要負起照顧者的責任,小小的年紀已很明白,也沒反抗,生活忙碌,也沒時間去抱怨;兩位妹妹年少,我只知要努力照顧她們。可是,原先在國內受人尊敬、生活充裕的爸爸,以為來港後可以繼續保持身分和工作,可惜夢滅,鬱鬱不得志,人變得性情暴躁,沾染惡習;媽媽在國內的身分、地位本來也備受尊重,但因某種原因而同意與爸爸一同來港,沒想到專業不保,生活也不保。父母壓力很大,彼此沒溝通,更不要說聽我們訴說,不是打、就是罵,女兒們也成為了他們發洩和傾訴對象。每天要看父親面色做人,總是戰戰兢兢的;媽媽在爸爸背後向我訴說他的不是,在爸爸面前又另一副咀臉,像是甚麼抱怨都沒有,我無法接受這兩副咀臉的媽媽。在得不到愛護、溝通的同時,我不但不喜歡他們,我更憎恨爸爸令我們家無寧日及媽媽帶來的負面影響。有時候,我會傻想我其實是有錢人家的女兒,我不想自己生於這種家庭,我更不喜歡自己。
身心受困,絕處逢生
如此成長,我不開心、不喜歡自己,心裡滿是憎恨,曾有人問我有否想過離家出走、自殘,甚至自殺,可有化憤恨為「力量」,作出控訴?事後回想,我也感到奇怪為何我沒有反叛,只知見日過日,充其量也只是跟一些男生往山上跑、劈山溪間的水管,或許,這個當時唯一的玩耍,也正好發洩了心中的負面情緒;加上讀書、忙於做家務、照顧妹妹、剪線頭幫補家計……每天都在忙,根本就沒時間停下來去計較、去抱怨。不過,日漸長大,有機會拍攝廣告賺多了一點錢,我就開始想到只要有錢,我就有能力離開這個家;而尋求愛的需要也令我很早就開始拍拖,也想過若有男朋友愛,我就可以與他共創一個家,不用留在這裡。
拍廣告、拍電影的日子,忙得令我沒時間去滿足心裡那份想離家獨立、脫離不開心的想法之餘,我卻參加了藝人之家的活動。原先缺乏自信、沒主見、如柳樹一樣隨風擺動的我,在參加了藝人之家的活動之後,心裡多了掙扎,明白到離家、同居、甚至為影藝事業犧牲色相,都不是我應為的事;我看到內在憎恨、不開心、不喜歡自己的心理狀態,源自我內心一份妒忌;極度掙扎之下,我決定放下這令我、令我家人不開心而大家都沒出路的妒忌之心,重新生活。
我學習成績不錯;能交上乖的同學、朋友;在藝人之家被愛護、保護;在接近錯誤的邊緣、在危難發生之際,都能擦身而過,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成長中或許有很多障礙,環境或有很多限制,內心卻隱藏著一種自己也不察覺的價值觀 —— 在限制、無望當中,正有很多無限的可能。爸、媽來港面對充滿限制的環境,他們迷路了,看不到那無限的可能,不能開心過活,也令我成為另一個不開心的人。我體會到生活中很多不可能並非偶然,最終總有出路,全是因為人的生命中都共同有一位不受限制、從不迷路,從出生就一直引領著、讓我總在有限中看到無限的神。
接受信仰,在藝人之家被造就,我愈來愈有自信,愈來愈警覺到引誘的呼喚,並曉得不為眼前的好處而放棄自己;縱然完成演藝課程,我沒有那種期盼在演藝事業「更上一層樓」的心態,反而想踏踏實實地工作及生活。
重修關係,遇上分離
終於,我沒離家出走,但我仍是為著妹妹,過得平靜一點。在不用被爸爸惡言對待打罵的情況下,我得到朋友的幫忙,自己置業,與妹妹搬離這個家,但仍繼續照顧媽媽。漸漸地,爸爸因在內地工作,也甚少回家,但不知從何時開始,他每次回家吃飯都要徵得我允許。
有一年的年三十晚,爸爸在電聯中得我允許回家吃團年飯,他因交通阻塞,在開飯後才回到,入屋後不但沒即時坐下,反而躡腳而行,走進洗手間沖身,只因他知我們不接受他身體發臭,不想我們不悅;一家之主,不但沒得到等候才開飯,更要自行進廚房取碗筷,坐下只夾面前的一碟菜及把碗裡的飯扒到口中,沒言沒語、沒之前的暴躁,更沒身為人父的尊嚴。望著眼前這位生我的父親,我心裡很難過,他不是曾多次在我批准之下才可回家吃飯的嗎?他不是多次被我們冷嘲熱諷他身體發臭的嗎?是我的忙碌令我忽略了他嗎?我不知道,只知在那刻,我那份斤斤計較的有限,被無限的愛心所溶化,不期然的問自己:為甚麼爸爸會變得如此?我又應否與他好好的傾談一下?
飯後,我與爸爸到碼頭散步,他那依然故我的急速步伐,仍令我心頭有氣,只是,這次走在他後面,我卻看到我的爸爸「縮水」了,不但是體型,更是整個人,像缺了甚麼稱之為人的東西。我覺得他很可憐,但其實是憐憫,他是我的爸爸,就算他不能表現身為人父的職責、身分,也應該是一個可以活得有尊嚴的人啊!我從沒想過,也情不自禁的向爸爸說了一聲 —— 我愛你,他即時的反應就是哭了出來,爸爸、男兒家、傳統的大男人,就在我這個不應看到他流淚的女兒面前流下他的男兒淚,我也不受控地哭了起來。那一刻,像是靜止了,我聽不到他說甚麼,我也想不起自己說了甚麼,像是:其實,我們都很關心你;其實,你可多些回來的呀……直至大家都把一切痛苦都哭出來。我體會到我能說出這句「我愛你」,是因為我真的仍愛他,只是為了幫家人討回公道,不嗤於他那種沒做好一家之主、給予家人愛的角色;另一方面,也想表現自己大家姐的身分,表達自己那份「你做不來?我來做吧」的心態。原來,我成了欺凌者,令爸爸不成人。這一句「我愛你」,我們和好了,我深信這可不是我一己之力能做到,而是因為我認識信仰、經歷愛的修復,能以無限的愛去與爸爸重建關係。經過幾年,爸爸回港都是約我在外見面,直至他明白家庭是由愛建立,又經歷了這份父女愛,他決定放下內地工作,回到這個家,與媽媽同住。
那天,我到車站接他回家,慣常步履急速的爸爸,因為肚子不舒服,用了可能是十分鐘的時間才從閘口慢慢的走出來。爸爸上車後,我先送他去醫院醫治不適,沒想到,一入醫院就出不了來(只曾一天回到家中),直至離世,因為他被確診末期腸癌。
爸爸接受手術後,傷口不能癒合,人變得更消瘦,我決定放低工作去陪伴他,達成他的心願,做他想做的事。差不多兩個半月後,爸爸送我一份寶貴的禮物 —— 接受主耶穌的救恩,就離世了。不是剛修補了關係嗎?沒好好相聚,卻那麼快就分離……雖然傷痛,但我再一次在人的有限中經歷那無限,就是確信我和爸爸會在天家相遇。
活在有限,經歷無限
從貧窮到生活得改善;從不堪一提到被認識的藝人;從沒價值到被重視;從爸爸離世前信主、因病留院不能回家至離世,縱然我每天去陪伴他,卻未能送他最後一程;又或是2002年開始的多次懷孕,我經歷了早產、三次胎死腹中及險些失去了兒子,原來,萬物都有它的時候。
那一年,我面對很大的工作壓力,也遇到很多人事的問題,還有錯綜複雜的辦公室政治,我對同事及機構的信任出現了很大的衝擊,在我腹中的兒子也每天隨著我心情的起伏而生活。在這惡劣的成長空間,他不但沒死去,更在32周出生。當時看著這個只有1.8公斤的「小」嬰孩,我心裡很是難過,既擔心他能否健康成長,也不知如何去照顧他,更因情緒不穩而影響餵飼。最後,我決定放下那會繼續影響心情的工作,不去思想經濟的問題,學習專心去照顧他,這些年,他從不利於成長的環境中健康地長大過來。
之後的兩次懷孕,胎兒不到兩個月就沒有了,我很難過,但也不得不接受,也接受了自己應該不會有機會再懷孕。直到第四胎,我在偶然的情況下知道懷孕了,我們既驚又喜,興奮於他的到來,卻又擔心保不住他。就像是如臨大敵一樣,我們決定請當時應該是最有名氣的醫生來照顧我這孕婦,製造適合這胎兒成長的環境,注射不同的針藥,為的是幫助胎兒能健康成長。胎兒大概五個月大,在一次普通檢查中,醫生說胎兒沒有了心跳,隨即寫紙給我去醫院引產。我呆了,也無法相信又一次的胎死腹中。一個人離開醫務所,負著一個死了的胎兒及千斤重的難過回家。我掀被蒙頭大哭,按摩腹部,推動胎兒,叫他不要睡。家人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幾天後,我決定去醫院引產,看著那已成型的兒子,小得連合適的衣服都沒有,我在過份冷靜中接受了他的離去,卻把痛苦的情緒發洩在丟掉一切為他來臨所準備的東西中,在為何用心預備也不能保護他的痛苦中哀悼。
在慣性小產、流產的情況下,後來我又懷孕了;在慣常被責怪是我沒好好照顧自己導致遇上早產、小產聲中,我選擇不告知別人這好消息;在醫生不看好胎兒能成長出生的情況下,我以順其自然的心態去懷著他,就算醫生多次暗示胎兒可能有缺憾、可選擇人工流產的,我也決定以平常心去走這段路,但仍會每早醒來確定他是否在活動才會起床。胎兒31周,看似要出來了,就算使用了一些催生的方法,他仍是在腹中卻不出來,到了38周,胎兒終於出來了,並發現臍帶打結,醫生說其實這胎兒是可以在腹中死去的。
就這樣,我再得一兒,也得到一個人生的提醒:我要謙卑下來,接受可以有的,也接受不能有的,因為聖經提到:「凡事都有定期,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。」
人到中年,面對很多有限,卻也同時經歷了很多無限,這些經歷也成為了別人的祝福,特別是幼時的貧窮、父女關係、懷胎生育,讓我學會在今日的生活裡、工作中,如何扶持那些在有限中的人發現無限,接受、放手或是一樣十分重要的謙卑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