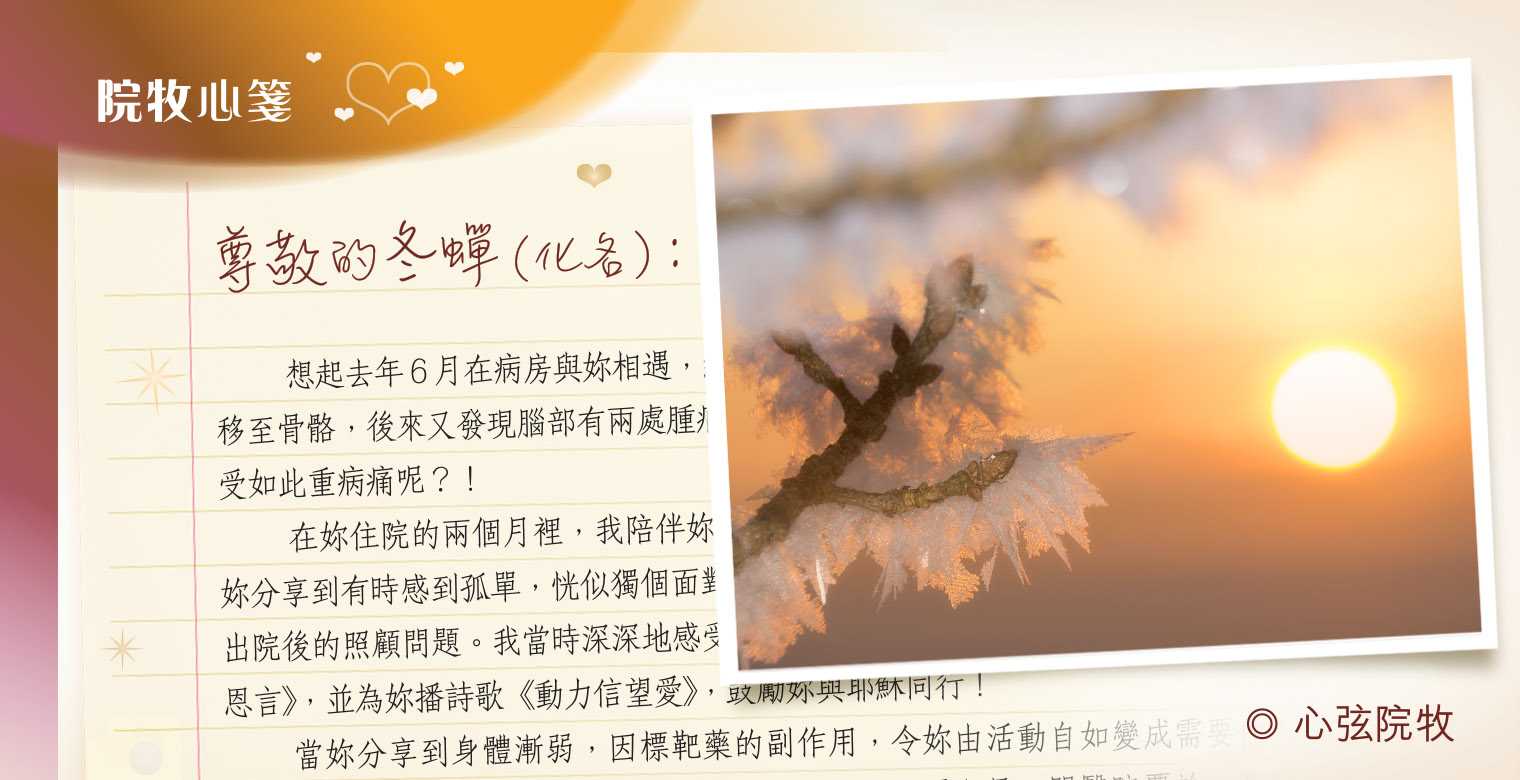
親愛的冬蟬(化名):
想起去年6月在病房與妳相遇,細心聆聽妳的故事,得知妳患有肺癌,而且癌細胞已轉移至骨骼,後來又發現腦部有兩處腫瘤,更有糖尿病纏身。聽到時心頭一酸,一個人怎能承受如此重病痛呢?!
在妳住院的兩個月裡,我陪伴妳走過一小段的人生路。我們十分投契,無所不談。當妳分享到有時感到孤單,恍似獨個面對疾病,加上標靶藥的副作用令妳嘔吐和腹瀉,又擔心出院後的照顧問題。我當時深深地感受到妳的孤單、無奈和擔憂。於是,我送妳一本《日悅恩言》,並為妳播詩歌《動力信望愛》,鼓勵妳與耶穌同行!
當妳分享到身體漸弱,因標靶藥的副作用,令妳由活動自如變成需要他人協助換尿片,是那麼難以適應的事!最令妳擔憂的是,必須要去另一間醫院覆診,深怕中途會腹瀉。我便播放詩歌《靠著耶穌得勝》來堅固妳的信心。感恩妳回來告訴我,整個覆診過程都沒有腹瀉。
還記起有一天,妳致電給我,說很擔心星期二做手術,害怕由小手術演變為大手術,甚至希望不用動手術。妳提起上次做手術前做惡夢睡不到,今次妳丈夫正在另一間醫院接受治療,妳很擔心他的情況。我感到妳正承受很大的壓力,便送上詩歌《倚靠耶和華》來安慰妳,妳說詩歌很悅耳,我就鼓勵妳在手術時也可倚靠耶穌,向祂祈禱。感恩的是,妳的手術順利完成,妳還告訴我:「沒有做惡夢,入手術室時自己有呼求主,所以沒有害怕,心裡有平安,將來出院後一定要返教會。」感謝主的保守,妳在一個多月後終於康復出院了!
冬蟬,妳出院後,我不時會想起妳,但總是沒有進一步行動去聯繫。直至數月後,妳致電給我說,教會有幾個人來訪問妳,妳不知如何應對陌生人,心情緊張,所以找我聊天。妳提到身體越來越虛弱,我便想翌日立即去探望妳,但妳說要視乎身體狀況,因怕不夠精神接待我。次日致電給妳,沒有人接聽。一個月後再次致電,也沒人接聽。腦海裡不斷浮現壞訊息:妳是否身體狀況突然惡化住院了?還是回了天家呢?三個月後,電話終於接通了,可是妳的家傭告訴我:妳走了!我反覆地回想妳與我最後的對話,妳說:「我很喜歡與妳傾談,因為妳很真誠,和其他人不同。」沒想到那次竟成為我們最後的對話!
冬蟬,謝謝妳對我敞開心窗的信任,妳的生命見證,教曉我「尊嚴」這一課,讓我看到妳生命的韌性,面對重重疾病,始終堅強去面對,無憾地走完妳一生的路程!
祝福妳在天家永沐主恩!
妳的院牧心弦敬上









